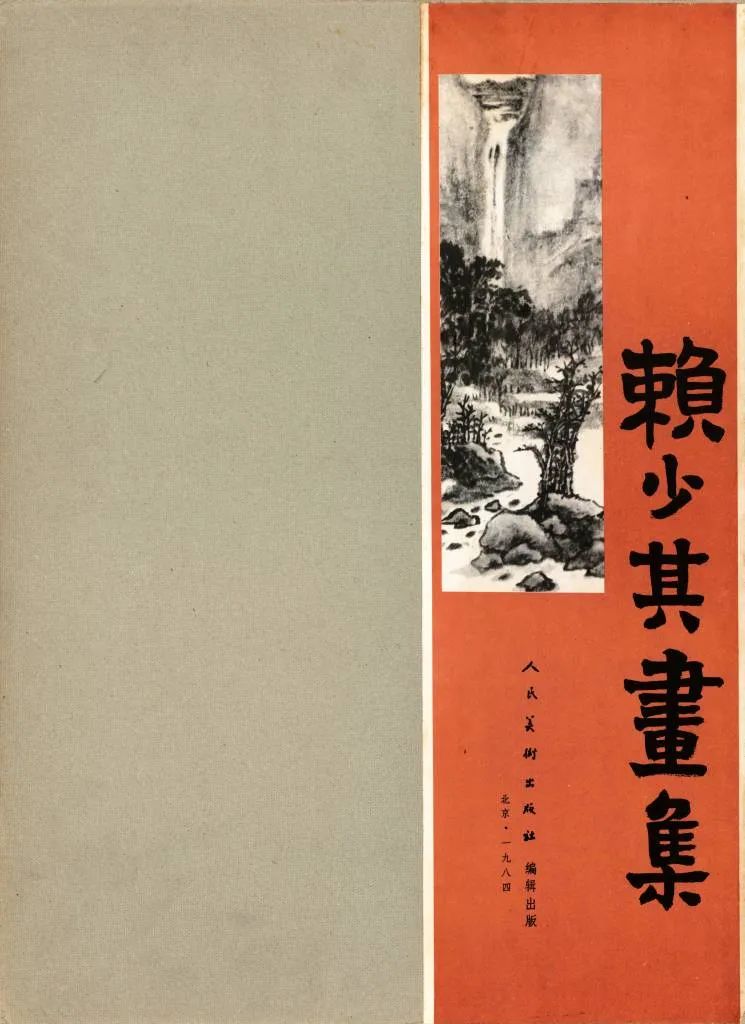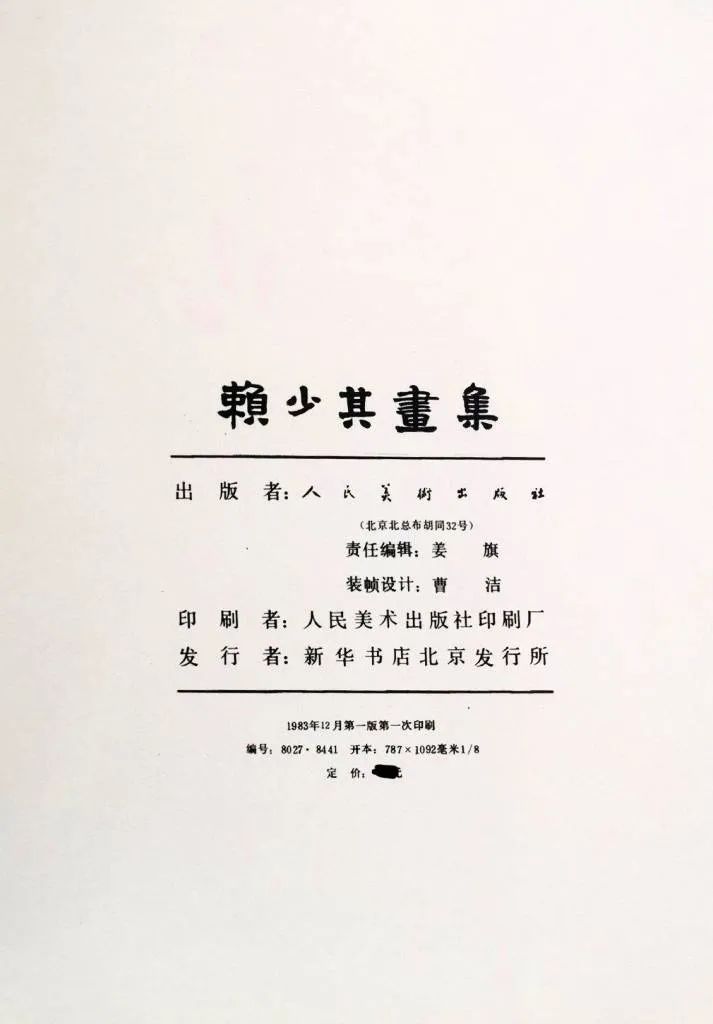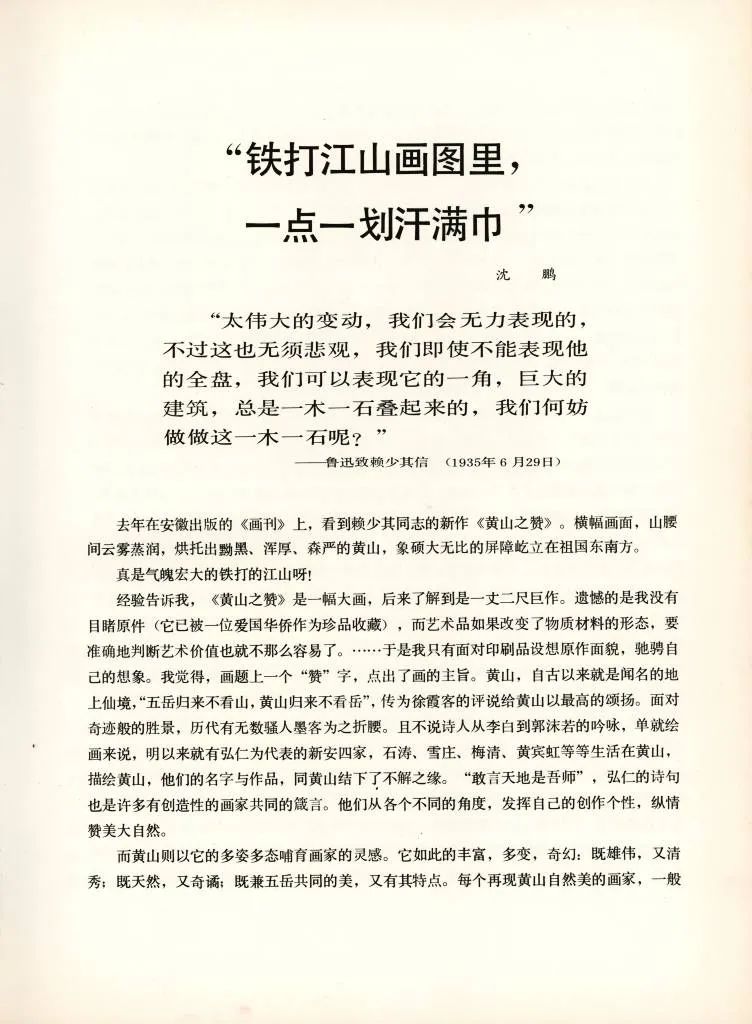沈鹏《铁打江山画图里,一点一划汗满巾》
发布时间:2023年08月23日
1983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赖少其画集》,沈鹏撰写一万余字的长篇评论文章《铁打江山画图里,一点一划汗满巾》作为前言,介绍了赖少其的革命经历、人格品质以及他在版画、中国画、书法、篆刻及诗词等多个领域的深厚学养和精深造诣,高度评价了赖少其的艺术成就和他对文化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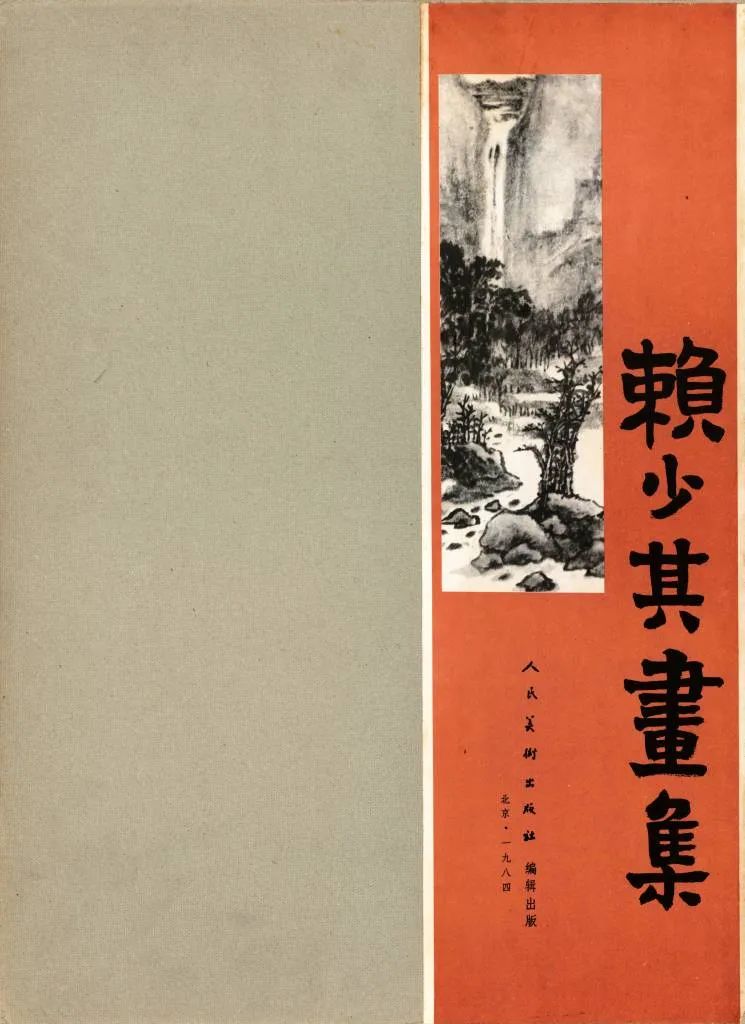
《赖少其画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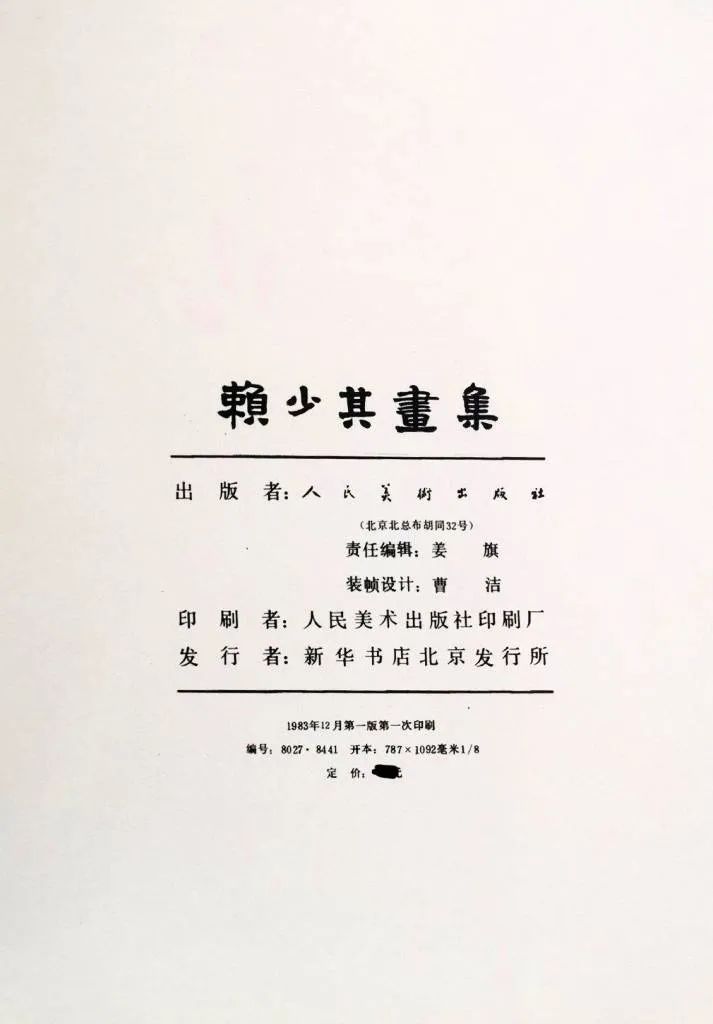
《赖少其画集》版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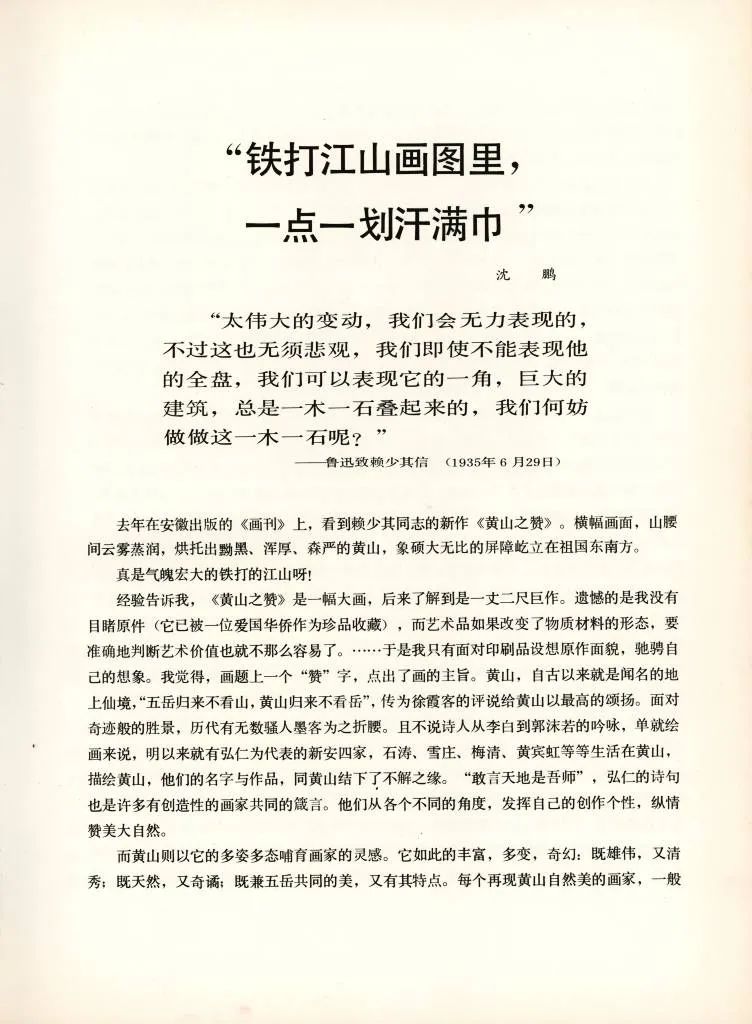
沈鹏文章
“铁打江山画图里,一点一划汗满巾”
沈鹏
“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去年在安徽出版的《画刊》上,看到赖少其同志的新作《黄山之赞》。横幅画面,山腰间云雾蒸润,烘托出黝黑、浑厚、森严的黄山,像硕大无比的屏障屹立在祖国东南方。经验告诉我,《黄山之赞》是一幅大画,后来了解到是一丈二尺巨作。遗憾的是我没有目睹原件(它已被一位爱国华侨作为珍品收藏),而艺术品如果改变了物质材料的形态,要准确地判断艺术价值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我只有面对印刷品设想原作面貌,驰骋自己的想象。我觉得,画题上一个“赞”字,点出了画的主旨。黄山,自古以来就是闻名的地上仙境,“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传为徐霞客的评说给黄山以最高的颂扬。面对奇迹般的胜景,历代有无数骚人墨客为之折腰。且不说从诗人李白到郭沫若的吟咏,单就绘画来说,明以来就有弘仁为代表的新安四家,石涛、雪个、梅清、黄宾虹等等生活在黄山,描绘黄山,他们的名字与作品,同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敢言天地是吾师”,弘仁的诗句也是许多有创造性的画家共同的箴言。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纵情赞美大自然。而黄山则以它的多姿多态哺育画家的灵感。它如此的丰富,多变,奇幻;既雄伟,又清秀;既天然,又奇谲;既兼五岳共同的美,又有其特点。每个再现黄山自然美的画家,一般说来只能描绘出黄山的一个侧面。可以说这是由于黄山本身的丰富,也可以说这是由于画家们有不同的创作个性。正如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和指挥《第九交响乐》的音乐家都以各自的理解进行再创造,不会重复别人艺术语言,道理是相通的。赖少其画黄山,有独特的风格。前面说过,《黄山之赞》赞颂祖国铁打的江山。这个印象,等我看过他近两年来的一大批新作有了更具体的感受。1981年11月,我去安徽,在合肥找到了赖少其的住处。我们虽早已是故交,但是到他居住的地方却还是初次。那是二层楼房的一角,他展出了一大叠新作,首先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勤奋,真难为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除了负担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先后七次上黄山,创作一丈二尺宽的大画十九幅,四尺三裁的作品一百多幅,还不包括大量的诗歌与书法。他的画里,有一幅题句分明是:“铁打江山画图里,一点一划汗满巾。”从后一句,我看到了他的勤勤恳恳、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从前一句,我体会他创造意境的匠心所在。真高兴,我从《黄山之赞》所“发现”的作者意图,在另一幅画上得到了“旁证”。画中山水,是画家本人人格的象征,是画家本人心目中的审美理想在山水画里的集中表现。如果说美学上的崇高与秀丽,壮美与优美作为相对立的风格而存在,那么我以为赖少其的风格应归属崇高、壮美一类。如果说山水画的“实境”与“虚境”作为两种对立的因素存在,赖少其无疑更注意于描绘实境。他爱用浓重的焦墨刻画被称为“黟山”(黄山石质黑,唐以前称黟山)的重峦叠嶂、奇峰怪石,有时辅以湿墨衬托出苍润青翠。他惯以立幅略带方正的画面便于显示高远与博大。皴法有时圆转,更多方折,在再现山石纹理结构的同时,流露画家本人的审美意识。作品中的理、法、趣是融为一体的。由赖少其画风,我联想到画史上的“北派”山水。有一次试着请教赖少其同志怎样看待历史上聚讼纷纭的山水画南北派之争,不等他回答,冒昧地先发了一番议论。我说,明代董其昌、莫是龙等人分山水画为南北宗,抬高“南宗”贬低“北宗”不免是狭隘的,客观效果缩小了山水画的审美领域。可是山水画发展史上确实存在分别为两种不同风格的流派。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画家描绘的客观对象不同所形成。以五代、北宋的荆、关、董、巨来说,荆浩隐居北方太行山,传世《匡庐图》以坚实的笔法画出高耸入云,四面峻厚的雄伟气势;关仝师荆浩擅写“石体坚凝,杂水丰茂”的关陕一带自然风景;董源则是“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所谓“一片江南”;巨然师事董源,专画江南“泼墨轻岚”之景。这里荆、关与董、巨所描绘的自然风景有明显区别,成为各自艺术境界与笔墨趣味的客观现实根据。倘以董、巨的笔墨画荆、关山水必定不伦,相反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山水画南北两派风格的形成,又同画家的气质、社会经历、美学观念等密切联系着。到过黄山的游客,无不被它的万千气象深深吸引,可是每个游客的美感经验不同,感受各有自己的侧重。有人盛赞黄山的雄伟,有人欣赏黄山的秀丽,有人沉迷黄山的奇幻,李白的一首诗突出黄山之高(“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郭沫若则有“深信黄山天下奇”之句。历来画黄山的名家,弘仁善用笔,石涛擅墨,黄宾虹则以笔为主兼施墨彩求其“浑厚华滋”。清初以弘仁为代表的新安派专画黄山,但新安派内各家画风不一致,查士标接近弘仁,而雄峻沉厚不及。孙逸与汪之瑞都有幽淡静逸的特色,而汪之瑞多用中锋简笔。好在画山水非为“案城域,辨方洲,标镇阜,画河流”似的描画地理位置。艺术表现的千差万别,反映了山水本身的丰富多彩,也体现画家多方面的主观意趣,足以满足观众多样的审美要求。山水画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一种形态,不应千篇一律,因为人的本质也不是划一的。以上,我谈了自己的认识向赖少其求教。他笑着说,他认为山水画园地里应当争奇斗妍。南北派之分,从艺术风格来看是历史的存在。壮美与秀美两种风格倾向,早在魏晋以来的山水田园诗里已经有了,在其他的艺术门类里(例如书法)也是存在的。赖少其很直率地说,他的作品倾向“北派”。我笑着说:你是南方人的“北派”画家,可见过去以画家出生地点区分南北派是多么狭隘!赖少其同志提示,形成他的审美意识有很深的根源。由他的话,我想了很多,思路回到初看安徽《画刊》上《黄山之赞》的感受,又从《黄山之赞》浮想联翩。我知道,任何一个艺术家风格的形成不是孤立的。“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鲁迅)那么,赖少其的思想与人格是怎样表现在画上的呢?是什么支配着他对于现实美的独特的感受和构思?为什么他笔下的黄山令人产生“铁打江山”的共鸣?……我渴望着对这些问题得到比较正确全面的解释。为了作出解释,我要求思想的翅膀飞得远些……终于,去年11月在赖少其同志家里,一个晚上,有机会听他长谈,他的夫人、生死与共的战友曾菲在一旁作了详细的补充。普通话里夹着乡音,赖少其追忆:1915年,他出生广东普宁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家乡在彭湃烈士领导下是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十岁刚出头,戴上红领巾成为“儿童团”的一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州美术学校学习时,是广州学生运动领袖人物。鲁迅先生热情地肯定他的小说《刨烟工人》并指出不足,引他走上革命文艺的道路,鼓励他以“一木一石”的精神从事艰苦劳动。还教他写作要“多看和练习”,在版画创作上继承民族民间传统,“多采用旧画法”。抗日战争时期,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囚入上饶集中营。经受过最残酷的刑罚“站铁笼”,战友们唱着他作的歌曲《渡长江》支持他坚持斗争。以后,同另一位美术家邵宇同志一起逃出敌人虎口,越过千山万水回到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抗日战争时期的作风,与战士同生死共命运。他担任一个团的政治处副主任,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立功运动”,得到中央肯定随后在全军推广,被认为是“连队政治工作三把钥匙”之一载入军史。莱芜战役后,被评为干部一等功臣,作为干部而得到这样大的荣誉,说得上是稀有的例子。全国解放之日,作为部队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参加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继而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天安门上检阅队伍的行列里,随中央领导人站在一起的就有赖少其。赖少其同志的脚步就是这样从时代的漩涡中,从满天风沙和弥漫的硝烟里走过来的,他曾自撰一副对联:“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表明他追求的艺术风格。可是我想,撇开句首的“笔墨”与“金石”,那“顽如铁”、“掷有声”,正好是他过去全部历史的贴切的概括。为着战斗需要,赖少其刻制大量木刻。1939年春节桂林家家户户贴的新年画《抗战门神》出自他的手下。可惜经过战火洗礼,除了《抗战门神》等少数作品还能在当年《良友》杂志一类刊物上找到,绝大部分荡然无存。赖少其同志给我找出一本1934年出版的《创作版画雕刻法》,编著这本新兴木刻史上第一本介绍版画技法的著作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灯光下,我从这将近半个世纪前发黄的小书里发现作者两幅刻画劳动者形象的木刻《月下》、《哪时才下雨呢?》,我发现,赖少其的神情深深地浸入历史的回忆中了,他用缓慢而深沉的语调说:“鲁迅先生当年寄希望于青年,表现了伟大先行者的远见卓识。是他,把我们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教我们从‘一木一石’做起,他连领取稿费之类的小事也教我怎样去做。——我们那时还非常年轻哪!”说到这里,又指着《创作版画雕刻法》里的木刻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那时有一股蓬勃的热情,至于创作技巧,不免是幼稚的。所以鲁迅先生给李桦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蔑视技术,缺少基础功夫,将会阻碍木刻的发展’”。赖少其同志在过去年代里毁于战火的作品无可挽回了。值得高兴的是那些作品已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木一石”发挥了作用,新文艺的大厦用无数战士的汗水建设起来了。与此同时,赖少其也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座精神大厦,它同我们时代的行程密切联结在一起,铮铮然“顽如铁”、掷地铿锵有声。青年时代的赖少其,大概几乎不曾想到后来会从事国画、山水画……那时普遍流行的关于中国画的观念,要么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国粹”,要么认为是落后的遗老遗少们的勾当。投身血与火的赖少其顾不上种种纷争,只是一个心眼,紧握刻刀与画笔面向穷人,予顽敌以致命的一击,虽然不乏形象的敏感性,可是当年新四军军部就设在黄山脚下的岩寺,却没有激发起他领略一下大自然美景的雅兴。当1941年与邵宇同志一起逃出上饶集中营,越过景色奇丽的武夷山,经过几昼夜摆脱敌人的追捕,也丝毫没有留下武夷山水的记忆的痕迹。他们心怀救国救民,忍受迫害、饥饿,当他们到达浙江丽水时,外表上已纯然是乞丐模样,怎能设想,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会成为他们的审美对象,进入他们的审美领域?直到全国解放初期,赖少其同志担任着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文联秘书长、上海文联党组书记等繁重职务,一如战争年代全力以赴,时常废寝忘食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然而赖少其不是那种埋头事务不问大政的人,他一贯地从实际出发,研究政策,探索艺术规律。全国解放初期,伴随着打烂旧的国家机器的进步要求,文艺界曾产生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不加分析一概否定的倾向,如何继承、革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画成为美术界的一个大问题。赖少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起先,以他的正直和热情尊重传统,爱护老画家;以后他的认识提到科学地评价历史遗产的高度,自觉地团结老画家。在南京,聘请傅抱石担任市文联美术部主任。不仅亲自到金陵大学授课,还说服南京大学学生听傅抱石讲课。在上海,他主持黄宾虹画展,代表政府赠予“人民画家”的称号,又为黄宾虹做寿,直到去世后举行葬礼。1956年,周恩来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成立北京中国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赖少其担任了筹组上海中国画院的任务。他对中国画的认识同党的政策完全合拍,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中国画家亲切地称他“知音”,结为“君子之交”。上面一段经历的重要性,一方面说明他做的大量组织工作对美术事业的贡献,不下于亲自从事创作;另一方面,这段时期虽然直接从事国画创作不多,但对后来成批创作国画形成自己的风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赖少其作品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黄宾虹的影响?为什么比较迅速地掌握了中国画传统的审美观并能出以深刻的表现?不能不同他在解放初期的活动有密切关系,这些活动比起一笔一画地临摹古人决非无足轻重,它大大地开拓了通向传统的道路,奠定了深厚广阔的创作基础。进一步看,以往全部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也为这些年来的山水画作了准备。如前所述,无论在皖南新四军,更无论在逃出上饶集中营的途中,我们的画家无心欣赏风景。实际上在整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赖少其以及许多共命运的美术家,用血汗为保卫祖国江山而战斗,却难得欣赏自然美的闲情逸致。后来呢?谁都知道,历史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从前的战士成了社会主人,祖国江山回到人民手里。人和自然的关系起了变化。自然面貌本身也日新月异,从前的破碎山河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大好江山。我们的画家足可以纵情挥洒,泼墨走笔。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人一般地都是用所有者的眼光去看自然,他觉得大地上的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的幸福和欢乐相连的。”全国解放后,美术工作者们以“所有者”的姿态看自然,使自然界成为美的对象,成了许多山水风景画的基调。赖少其的作品无疑地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他的全部生活、艺术实践决定了他在共性中有自己的个性。“铁打江山画图里,一点一划汗满巾”。——不知为什么,每当反复回味赖少其同志画上的题句,我总是把他今天笔下的黄山同当年保卫祖国江山联系起来。当年,为保卫祖国江山不怕流血;今天,为描绘祖国江山不惜流汗。两者之间决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倒是蕴藏着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它们体现了作者的完整的世界观,包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顽强执着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探索精神等等,都是统一人格的具体表现。进一步说,今天的艺术实践是过去生活实践的继续发展。没有长期生活实践培育起来的思想境界,产生不出“铁打江山”的构思与意境。——因此要说赖少其的绘画风格倾向崇高的美,恐怕单从山水流派的师承关系找寻根源是远远不够的吧!就说艺术本身的渊源吧,风格的形成也决非仅仅得益于传统的中国画。自然,这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多方面艺术修养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他学生时代即开始写小说、新诗、散文;编过剧本《集中营里的斗争》;出版艺术评论集《文代归来》、《为了把艺术献给人民》。作为书法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此外,他还刻制过一千多方印章,是一位篆刻家。赖少其的多才多艺,使得各门艺术间互相渗透成为必然的趋向。自然人们更不会忘记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版画家名世。1959年,他由上海调安徽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民间套版简帖引起他的注意,各处搜访编成一本精美的画册出版。他组织本省的几位中青年画家(师松龄、陶天月、张弘、林之耀等)一起为人民大会堂刻制了一批被称为“新徽派”的大型套色版画。新颖的题材内容,丰富的色彩,雄健的气魄,浓重的装饰风,在版画领域里别开生面,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赖少其的中国画。我觉得,如果不把他的“新徽派”版画同近几年的中国画孤立地看,那《黄山后海》、《淮北变江南》等版画作品已经萌生着今天所画黄山的意境与情趣。在版画中吸收了中国画皴法与线描,反之,作者的中国画又分明从版画里吸取了营养,例如黑白的强烈的对比,线条的粗犷老成,装饰效果的运用,都同版画功底分不开。有些作品皴擦,几乎吸收了版画多层次的刀法,愈益显出庄严厚重。有一次,他指着一幅描画始信峰的新作,向观赏者发问:“你看有没有铜版画的味道?”可见他作品中的版画风格是有意识地追求着的。赖少其作为书法家,同作为版画家一样,比直接从事中国画创作要早许多年。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先生给他复信所写的熔铸晋唐,谨严方正的蝇头小楷,大大鼓舞他练字的兴趣,坚持几十年从不间断。书法史上的“碑”与“帖”之争,有的纯属门户之见,他不理会。但他告诉我,书法如同绘画,倘按风格划分南北派,他更倾向于北派。先前,他的兴趣在王羲之父子,曾反复练习《兰亭序》,以后又转向欧阳询,又学郑板桥、伊秉绶、邓石如,又醉心金冬心,终于以金冬心为仪范,心慕手追、穷本溯源汉魏法度。方笔取劲利,转折处掺以圆浑,大至擘窠榜书,小至细如髭发的真书,一丝不苟地透露出雄厚的力感。他的“金冬心体”的“漆书”端庄凝重,而行书则流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素养精深的书法为他的中国画起到奠定根基的作用。中国画历来讲究“笔墨”,其内涵可以包括狭义的技法与广义的技法两个互相联系的范畴。前者较多地直接体现造型能力,后者较多地体现一整套反映生活的传达方式与审美趣味;两者都同书法有直接关系。单从技法的角度来说,他的笔无妄下的勾、斫、砍、点、皴,体现了书法的力度,至于置阵布势到气韵神采,得之书法的就更多了,不过有些是有形的,有些属无形。诗、书、画兼长的艺术家赖少其的可贵,不但在多能,更重要的是善将三者融为一体。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不必每幅画非题诗不可,或每首诗必须配画,主要看画有无诗意和诗有无画意。作画不追求诗的意境,画完后生凑诗句,恐怕不易感人;同样,作诗不注重画意,作完后配上说明性的绘画,很难说得上真正的诗画结合。文人画要求的诗画结合,是两种不同体裁的有机统一,创作之前,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落笔完稿体现为完整的意境。因此诗画结合,要求贯穿创作过程始终,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的环节,笔墨技巧的发挥便有了广阔的天地。诗人气质,是赖少其同志身上很可宝贵的特质。歌德的《谈话录》曾反复阐述与“情境”很接近的“母题”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庸人设想只要学会作诗技巧就算尽了诗的能事,真正的诗人善于从生活里发现诗意,“把所有的母题集中起来”。赖少其属于这一类诗人。他善于从平常景色里发掘出真正的美。众所周知的名胜地,一般说来具有典型意义的美,他不轻意放过;但更留意习见的断崖、云雾、山石、流水、树木……一经点化,自成一番气象。或是以瑰丽的想象引人入胜,或是突出山势的博大、高耸,或是渲染云水的苍茫、空灵,或是松涛滚滚、繁花似锦……总之“登山则情溢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的思想的火花一接触到生活,随时随地能够触景生情,生发出诗意。我们随手拈来一些题画佳句:“有泉万壑响”,非亲临其境又有深入细致的感受不能写出;“秋山积雨晚来凉,白云绕屋生流泉”,静中有动,山中特殊气氛跃然纸上。“为因送行客,红叶满山坡”,山上的红叶通人情,读者油然记起“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名句。“既到桃花源,何必问秦晋?”真是超绝人寰,有意想不到的巧妙。在这些诗句里,移情入景,借景抒情,处处表露诗人的敏感、天真、浑朴,别人的语言无法取代他的情感真实,无怪作品在香港展出时有的评论者指出:作品不仅再现黄山,而且是有赖少其风格的黄山。在赖少其身上,诗人的气质与战士气质融洽无间,除了从全部经历找出最有力的佐证,作品本身同样颠扑不破。本文开头提到的《黄山之赞》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诗人气质里未尝没有战士气质。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不论采取何种构图、笔法,发而为诗,真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且举一首1980年5月登莲花峰观皖南事变故战场写的《凭吊》,诗人纵观历史,豪情激越,谱出一位亲历事变的勇士之歌:赖少其许多诗作不按格律,词也是“自度曲”,从用字遣词的角度读者完全可以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可贵之处在于不斤斤计较细枝末节,紧紧抓住“母题”一任热情奔放驰突,直到言足以“达意”、“言志”后已。《凭吊》一诗,已由音乐家沈亚威谱成乐曲,可是至今我还未看到与诗相配合的绘画,也许能用诗写出来的不见得适合以视觉形象再现。可是在广泛的意义上,画家赖少其笔下的面貌众多的黄山,已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一支宏伟的交响乐,其中包蕴着《凭吊》的灵魂。《凭吊》的主题曲以各种变奏出现在众多的画面上了!我把赖少其同志看作一位真正的诗人,是因为他的作品出自肺腑,直抒襟怀,非同娴于词令却矫揉造作的靡靡之音。我国古代论诗文重“风骨”,反对拘于声律“伤其真美”,论画重“意境”,所谓“发于墨者下”。诗论、画论有共通的道理。赖少其所追求的,超出了音韵平仄与一笔一画,虽然,他在技巧上也还有可改进之处。赖少其画黄山,在表现主观情趣的同时,注重忠实客观对象,不因强调写情而忽略写景,以及强调表现而轻视再现。他有句警辟的经验之谈:“画黄山要注意一个大字和石纹变化的特点。”从“大”处入手才能显出气势;曲尽“石纹变化的特点”才能体现黄山特点以及黄山各个山头特点,摆脱老一套的公式,他从实践中得出的真理,正好与古人“远看取其势,近看取其质”的诀窍一脉相通,合乎徐悲鸿先生常说“尽精微,致广大”的妙理。深入观察“石纹变化的特点”,赖少其的画笔跟着山石变化不断改变着方折、圆转、侧笔、中锋,斧劈皴、解索皴…… 一切以如何反映客观对象的本来面貌为转移。他很欣赏贺天健说的要从具体画一块石头去掌握黄山石纹特点。在一幅《始信峰》的画上写道:“始信峰为黄山精华,多少画家从这块石头得到启发,其艺大进。我反复写之,总觉新鲜可喜,可谓画家瑰宝也。”由一座山峰的石块得到启发,“反复写之”,画家的“尽精微”的精神没有脱离“致广大”的要求,或者说,尽“精微”是为着叫“广大”建立在更加坚实牢靠的基础之上。赖少其画山水,千方百计使局部服从整体。采取俯视和散点透视,调动疏密、虚实、起伏、开合等对立统一的因素形成崇高感,以“大”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敬赞。画家深知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要注意画出黄山的“大”,但难在绘画不等于生活,想把生活里的黄山简单地“如实”搬进画面是做不到的,但画上的黄山又要体现生活中的黄山。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黄山太大了,画在纸上,大变小不容易。”有次他创作一幅以温泉一带山水为背景的作品,有人认为此地多溪泉瀑布,应突出画水,可是我们的画家却说:“水画大了,山就小了,显不出山势的雄伟。”由此一例也可说明赖少其作画时处处要求“雄伟”的美;“大变小”之难,难在“小”中见“大”,难在源于生活又比生活更高更美。读他的山水画,我总感到视点很高,让千岩万壑统摄眼底,以充分感受为前提重新安排山水草木和亭台建筑,必达“咫尺有千里之势”后已。为着这个目的,画家的技巧、手法也并不是限定在一个框子里,同是体现崇高感,每幅作品立意不同,有的强调石质的坚硬(如《渡仙桥》),有的突出林木深秀(如《下临深渊》),有的打破苔点“攒三聚五”的老办法,用密集的墨点造成特殊效果(如《铁打江山画图里》),有的虚而不实,以虚托实(如《画不尽,风和雨》)。此外,也还有曲径通幽、一角平畴的景象(如《探幽图》、《湖阔鱼龙跃》)。自然界的山水无比丰富,我们敏感的画家换一块地方,换一个时令,换一种气氛,会有意无意地改变画的气质,用惯了沉重的笔触,有时也会出现轻丽明快的线条。但重要的是凝聚在性格中突出的,稳定的因素不轻易改变——一切自有“我”在。赖少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向传统的学习,他对待传统一贯采取十分审慎、认真的态度。我认识的画家中,颇有一些由西画入手兼长国画的高手,采取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成就各有千秋。赖少其作为一个西画家,是如何登入国画堂奥的呢?前面说过,他很早就同中国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受了传统艺术的美学观念很深的熏陶。但是正如他对待任何一门学问一样,喜欢从根本上做起,不取巧,不抄捷径。他曾说:“兵无武器难称雄,不学传统空唐突”,虽然对生活有所体会,如没有恰当的表现技法依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当他确信自己掌握了“武器”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创作。虽然,他决不反对并且实行着边干边学,一面创作一面提高技巧。临摹是赖少其掌握传统的重要手段,1959年赖少其调安徽省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任职不久,偶然在歙县发现皖派篆刻家程邃的山水册页,这一发现无异打开了进一步通向传统的坦途。垢道人的干笔渴墨、苍茫简远的画风立即吸引了他,短短半年里一连临习几十遍。现在保留下来两本,是他最得意的,看过的人都说几乎可以乱真。他珍视程邃山水册临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自己的创作,说由此可以看出他如何登堂入室。他认为“一张画临一次比看十次印象还深,临了领会才真切”。他用临摹的方法,广泛学习戴本孝、唐寅、龚半千、梅清等画家的技法充实自己的笔墨根底,并在创作中消化吸收。另方面,临摹对他来说只当作登堂入室的一种手段。六法之一的“传移摹写”,原本是摹画的手段,以后发展为临习古画学习传统的一种方法。历史上中国画曾经在陈陈相因、脱离生活的风气支配下,滋长了以“流”代“源”,以摭拾古人唾余替代深入生活,临摹曾被一部分画家认为是不可取的,对如何学习传统也还有争议。但是我想这不等于全盘否定临摹,最重要的要看画家对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摆得正确与否。是以古人的笔墨替代创造,还是从创造性地再现生活出发学习古人?赖少其同志无疑属后一种态度,他没有颠倒二者关系。以下是他画上常见的题句:“古人有此法亦行,古人无此法亦行。法从实践来,法乃实践之总结,人各有法,此之谓历史。”经过长期悉心体察,赖少其看出了自新安派到黄宾虹一代又一代画家的独创性技巧与客观生活之间生动活泼的联系。他说,古人画黄山从生活中来,我们要从传统中探出生活的源,即由古人作品中看出前代画家如何从生活出发创造笔墨技巧。他在一幅画上题道:“萧云从有此法,全从生活中来。”只有对传统技法有深切体会并对生活实景作认真观察的画家才说得出这样的话。他又说,临摹古人先求“似”,然后求“不似”。“似并不易,不似更难”、“余仍在似与不似之间,知路途之遥远也。”他的话,一如有些画家常说的学习传统要“以最大力量打进去”、“酷肖原作”,然后“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取原作之精神”,差不多一个意思。饶有兴趣的是,从前的画家也爱说“似”与“不似”一类的话,齐白石主张“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说的是绘画与生活的关系,赖少其说的则是创造与继承传统的关系。不过两者都可归结到一个共通的道理——绘画应当源于生活,又比生活更高,更美。“不似”传统,意味着要“似”生活,以生活为唯一的源泉。主张“人各有法”,志在独创的赖少其,一贯地尊重生活,尊重传统,尊重前人和当代人的创造成果。他那不平凡的经历,诗人的气质,战士的豪情,多方面的素养,为开辟独特的艺术道路创造了前提。他的画、诗、书法——“自有我在”,但是他未想过要把“自我”孤立于客观生活之外成为艺术作品中唯一的存在。他从掌握生活与艺术的客观规律中找到表现自我的广阔天地。赖少其同志就是这样认定方向,积累创造成果,攀登黄山天梯,探寻艺术之源。这本画册里的作品,是近几年的小结,又是向高处迈进的新的起点。当有人请他谈谈艺术经验,回答的是一段非常朴素的话:“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我只是觉得要学点什么,做点什么。要做就动手做,不要等待。条件允许你搞什么,你就抓紧搞什么,而且把它坚持下来。”谈话的主要之点,我体会还是鲁迅先生当年教导的“一木一石”的精神,可贵的是赖少其同志能够持之以恒,保证他向着艺术的峰巅不停步地迈进。注:本文原载于《赖少其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